
文/董小玉 何艳
“观看先于言语。儿童先观看,后辨认,再说话。”约翰·伯格在《观看之道》开篇的这句话语,犹如雷鸣般振聋发聩,重塑我们对视觉的价值体认。这部诞生于 1972 年的文化巨著,脱胎于 BBC 同名电视系列节目,一经问世便引发全球轰动。其译本如星子散落,覆盖数十种语言版图,不仅稳坐全球艺术院校核心书单,更成为滋养数代学人思想的精神沃土,在艺术批评与文化研究领域树起不可逾越的丰碑。《观看之道》的革命性意义,在于它以锐利的智识之剑,劈开 “观看” 这一日常行为的表象,剖析出背后潜藏的权力网络与意识形态密码,成功将大众从视觉消费的被动受体,锻造为具备批判自觉的文化解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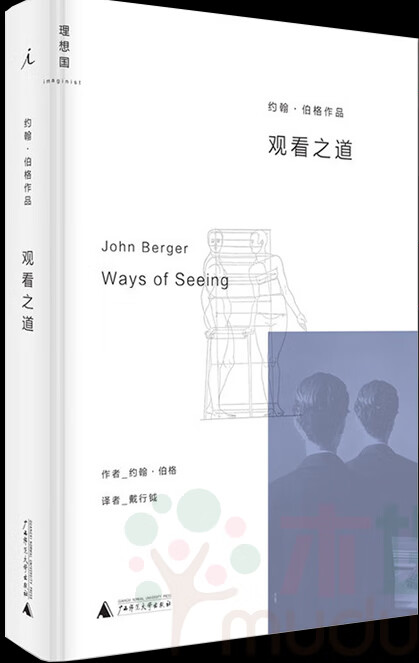
解构视觉神话:观看是感官与思维的结合
伯格最根本的颠覆在于揭示了观看行为本身受制于历史和社会条件这一本质现象。我们习惯于认为“眼见为实”,并将视觉视为最直接、最真实的感知方式。然而伯格却指出:“我们从不只是看一样东西;我们总是在看东西与我们之间的关系。”观看的意义,或许就隐藏在凝视与被凝视之间的关系上。维特根斯坦也认为看似简单的“看”其实包含复杂的认知活动。
在分析欧洲裸体画传统时,伯格展示了男性凝视如何被自然化为普遍的观看方式。他指出:“男子重行动,女子重外观。男性观察女性,女性注意自己被男性观察。”这一简单的观察揭示了艺术史中隐藏的性别政治——女性被客体化为被观看的对象,而男性则占据着观看主体的位置。伯格的分析不仅适用于古典油画,也同样适用于当代广告图像。当我们今天浏览社交媒体或商业广告时,这种视觉权力的不对称分配依然清晰可辨,足以证明伯格的批判视角具有惊人的时代超越性。
更激进的是,伯格祛除了艺术“灵光”的神秘性。在本雅明的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艺术作品的权威不仅来自其独特性,更来自一整套博物馆、艺术史、拍卖行等制度所赋予的社会价值。如今,梵高的向日葵被印在咖啡杯上,蒙娜丽莎成为表情包,伯格所预见的正是机械复制时代艺术神圣性的消解过程。这种解构不是价值的贬损,而是将艺术从神坛拉回人间,使其成为人人可以参与讨论的公共话题,并具有了社会价值。
视觉的资本逻辑:当观看成为商品的占有
伯格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延伸至视觉领域,提出了一个震撼性的观点:观看方式反映并强化着财产关系。在欧洲油画传统中,肖像画和风景画不仅仅是艺术藏品,更是财产清单和所有权声明。“油画要歌颂私有财产。它本身就是一份属于某个人的财产,而且它描绘的也是财产。”这一洞察揭示了艺术形式与社会经济结构之间的深层联系。
这种视觉占有在当代社会演变为更加隐蔽的形式。广告图像不再直接展示财产,而是创造欲望和缺失感,将观看转化为永不满意的消费循环。伯格尖锐地指出:“广告关注的是人际关系,而不是物品。它承诺的不是快乐,而是快乐的可能性——在他人眼中显得快乐的可能性。”这种分析解释了为何在物质丰富的时代,广告反而更加无处不在——它不再销售产品,而是销售通过他人眼光确认的自我形象。数字时代更将这种逻辑推向极致,社交媒体使每道目光都蕴含经济价值,“点赞”与“观看量”成为新货币,我们同时是观看的消费者与被看的商品。伯格40年前的洞见,为我们理解当下疯狂生产与消费图像时究竟在参与何种关系的再生产,提供了至关重要的钥匙。
抵抗的视觉:重建观看的平等对话
伯格积极探索视觉实践解放的可能性。他推崇那些打破常规观看方式的艺术实践,如弗朗西斯·培根扭曲的肖像,或纪录片摄影师对边缘群体的呈现。这些实践的重要性在于它们“不是邀请观众占有被描绘者,而是邀请一种平等的对话关系”。
伯格对摄影的讨论尤其具有启发性。与油画不同,摄影本质上具有民主潜力——它不依赖于长期训练,可以捕捉未被编排的现实,能够无限复制传播。伯格认为:“摄影师做出的选择不是绘画性质的选择,而是程序性质的选择,更像是见证人的选择而非演员的选择。”这一特性使摄影可能成为抵抗视觉霸权的工具,尽管它同样容易被商业和权力收编。
在当代语境下,手机摄影和社交媒体的普及实现了伯格的愿景。普通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图像生产能力,传统视觉权威被不断挑战。阿拉伯之春中手机拍摄的抗议画面,黑人运动中流传的警察暴力视频,都验证了伯格式的“抵抗视觉”在数字时代的生命力。然而,这种民主化也伴随着新的问题——图像泛滥、真相危机、注意力经济对人的捕获。伯格的思考提醒我们,技术本身不具解放性,关键在于我们如何使用它,以及我们发展出了怎样的视觉素养来驾驭它。
“在一个被影像包围的世界里,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学会观看。”伯格的这一警示在今天显得尤为紧迫。《观看之道》出版近半个世纪后,我们生活在一个视觉刺激前所未有的时代,但我们的观看能力是否真的进步了?我们是否能够穿透图像的表面,理解其背后的多层深意?使“心中之眼”明亮起来。
法国思想家福柯曾说:“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时代,而是讲述话语的时代”,这可以是为约翰・伯格《观看之道》量身定制的注脚。这部诞生于视觉革命前夜的经典,不仅是解剖 1970 年代视觉政治的锋利手术刀,更锻造出穿透时空的分析棱镜 —— 当 AI 绘图的算法迷雾、深度伪造的数字陷阱,以及虚拟现实的感官茧房重构人类视觉认知时,伯格对观看机制的批判性解构,正以惊人的预见性洞烛当代视觉困境。这种将 “观看” 从本能行为升华为反思性实践的智识突破,本质上是一场关于认知主权的隐秘革命 —— 当我们开始叩问视觉经验的建构逻辑,实则已悄然改写着人类与世界对话的底层代码。



600bd524-6a81-498b-8e10-6aff1cc18895.jpe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