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董小玉 何雨轩
数字技术的浪潮裹挟着人类步入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交图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不但可以克服时空障碍,并且能够通过微信消息还原语言,视频通话还原相貌,VR还原现实场景。在这个“永远在线”的时代,北京大学邱泽奇教授的《重构关系:数字社交的本质》如同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剖开数字社交的肌理,用生动的案例揭示其如何重构人类社会的基本关系—家庭、朋友、工作与生活,为理解数字社交的本质提供了兼具理论锐度与现实温度的新视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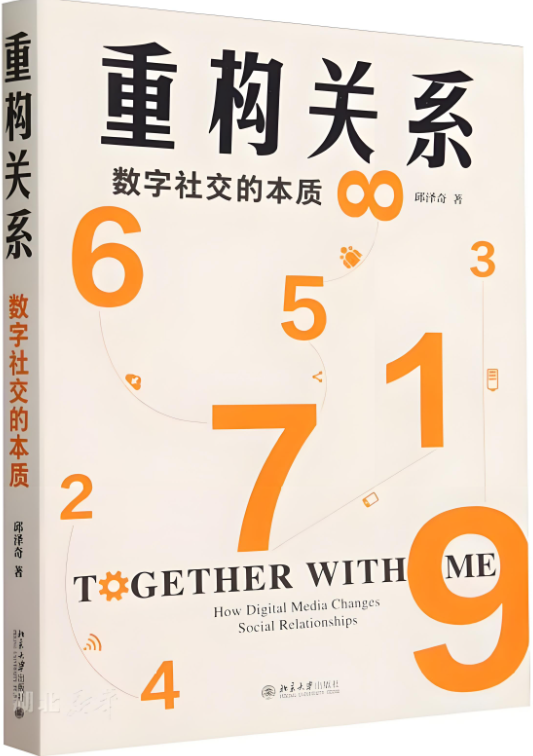
从“身体在场”到“数字同场”的关系建构
在未有文字记载的早期人类社会中,人际间的具身化交流局限于物理空间的范围之内。随着文明的进步,文字作为物质化的交流媒介应运而生,它使得信息与思想借助符号的力量,得以跨越地理上的重重障碍,实现了远距离的传播与交流。而数字时代的连接泛在,彻底消解了时空桎梏,使个体得以编织一张以自我为中心的全球关系网,个体与社会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以个体为中心进行资源组织”正在成为新的个体与社会关系的特征。在连接泛在前提下,个体可以随心所欲地与世界上的任意对象建立关系,当然,人们对数字技术的过度依赖,也引发了一些学者的担忧。
从表情包到视频通话再到虚拟现实,人们不断利用愈发先进的技术模拟身体,以缓解身体不在场的缺憾,弥补情感表达的缺失,但这种身体缺席的交流仍然引发了焦虑和不安。雪莉·特克尔曾在《群体性孤独》一书中曾向社会发出警告,认为数字技术重创了人们的情感与心灵,带来了“情感泡沫”。针对特克尔的悲观论调,作者提出了更加乐观的视角。他质疑将“身体同场”视为实现群体性的唯一路径,指出“数字同场”亦是满足人类群体性需求的有效路径。在书中,何瑜通过电子邮件开展“码里恋爱”,建立属于自己的亲密关系;施翘不断适应数字交流规则维系与男友的亲密关系;许俊熙在互联网上进行语言cosplay满足了自己的兴趣追求;高考失利的程慕馨利用数字链接突破了科层岗位,拥有了更多可能性。在自我社会下,个体围绕社会的社交转变为个体汇聚关系的社交,技术给予了个人与任意对象建立关系的机会,并使得个人能够在自我建构的关系中获得自身期望得到的价值和意义。
技术赋能与功能异化的思考
技术发展具备双重性,一方面是技术的赋能,年轻人通过算法匹配“搭子”,精准满足健身、观影等细分需求;职场人士挣脱地理束缚,在云端构建跨国协作网络;独居老人借助数字设备,将“每周探望”升级为“时刻在场”。另一面则是异化的暗流,朋友沦为功能模块,亲密关系退化为情感代餐,工作以“隐形加班”侵蚀生活边界。当关系成为可定制、可替换的“数字零件”,情感的深度与重量或许便悄然消逝。
面对数字社交关系的复杂性,作者提出“建构积极和包容的生活关系”。正如社会人类学教授项飙“重建附近”的呼吁那样:在迷失远方的摇摆中,从具象的、周边的生活中重建交流与互动,来汲取一些前行的力量。患口吃的陈妍通过舞蹈社的微信群重获表达自信;肢体残障的白彩凤通过直播建构了自己的生活世界;双目失明的裴子欣通过线上心目影院找到了同龄伙伴;数字移民张秀梅接纳数字技术找到了自己的老年生活新阵地。书中的一个个鲜活案例揭示了一个道理:技术本身并无善恶,数字技术下的个体并非完全孤独,关键在于个体如何把握技术这支“笔”来叙写何种生命价值与意义。
在数字浪潮中锚定自我
人类社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深度媒介化进程。智能设备成为“新器官”,AI技术不断进化成为“第二大脑”,算法的滥用异化了人们的思维,交往甚至劳动……人类浸身于信息的海洋中,一举一动所留下的数据都如滴水归海,偏见、焦虑、不平等在数字暗流中悄然显现,人的主体性受到了巨大冲击。这提醒我们,数字技术重塑的不仅仅是社交关系,更是人类的存在本质。就像韩炳哲在《非物》中讲到的那样,“我们不再安居于大地和天空,而是居住在谷歌地球和数字云之中。”信息的流动和去形化使得一切变得虚无缥缈,任何东西都失去了牢靠朴实的手感,数字技术剥夺了身体感知的交流,让真实的面对面消失于无形,只剩冰冷的数字和代码。
然而,面对数字浪潮下的各种变化,无需恐惧于未来的不确定性。正如作者所言:“对生活关系的重构,不是奔向自由与独立的欣喜,而是形塑人类新生活的机会。”个体如何选择,决定了他们的道路是通往孤独,还是通向幸福。或许真正的自由,在于清醒认知技术的赋权与带来的挑战,在“连接泛在”的海洋中,以主体性为锚点,编织一张既积极包容、又保有温度的关系之网。身处数字时代浪潮的我们,不仅要成为技术的使用者,更要成为其创造者和引领者。通过不断反思和探索,在科技赋能下,寻找到属于这个时代的生命意义与价值。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这场前所未有的变革中,锚定真正的自我。



600bd524-6a81-498b-8e10-6aff1cc18895.jpe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