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董小玉 何芝娟
“记忆是活生生的生命,处在持续的生成之中,对‘记与忘’的辩证关系始终开放。” 这是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留下的箴言。提起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惨痛记忆,我们常强调“不可忘却”,但现实的复杂超越了记忆与遗忘这一组简单的二元对立模式,因为“历史不会自己说话,它只能依靠人们的言说”。李红涛、黄顺铭合著的社会科学著作《记忆的纹理:媒介、创伤与南京大屠杀》一书便是从这里出发,以史为经、以不同媒介场景为纬,考察南京大屠杀创伤建构与记忆形塑的互动过程,带领我们思考:如何反思我们建构南京大屠杀的记忆实践?为建设面向未来和光明的民族共同体,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南京大屠杀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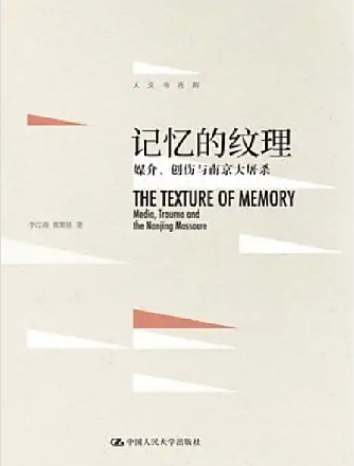
撕开伤口:历史在媒介中被书写
本书开篇就对各个阶段里南京大屠杀媒介记忆书写进行了细致的梳理。1937年,西方记者在报道南京大屠杀时称其为“地狱般的四天”,将这场暴行首次带入全球视野。国内报章《大公报》则发布社评《为匹夫匹妇复仇》,这是对日方侵略者暴行的愤怒控诉,也是战时进行民族情绪动员的重要工具;战后审判中,对受害者人数“20万+”与“30万+”的讨论则更加体现出话语权的争夺;在冷战阴影下,这道记忆伤口经历了荒诞扭曲,沦为斗争的工具;中日建交时,却又被强行贴上“友好”的创可贴,在“中日友谊”的叙事中被淡化;直到1982年日本教科书事件,这段无法被国人忘却的伤口才被重新撕开,并在《人民日报》的“耻化报道”中与民族复兴相结合,再次出现在公共视野。及至当下,国家公祭日正式创立,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创伤记忆以一种制度化的形式作为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不断鞭策着后人勿忘国耻、我辈自强的心志。
南京大屠杀的记忆在这八十多年的流转中不断变形:最初,它是幸存者难以启齿的个体记忆,是地方层面的伤痛;后来,它上升为国家记忆,成为民族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它已被纳入“世界记忆”,被写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档案。战时的媒体强调“复仇”,战后的法庭诉诸“正义”,新中国成立后则突出“国耻”……每一次叙事的重组,都意味着遗忘与记忆的重新分配。
作者通过对这段历史的梳理提醒我们,这一路径并非只是自然沉积的历史事实,在媒介的书写中经历着复杂的变形与重构。的确,因为事实的残酷往往超出语言的承载力,媒介对于南京大屠杀的记忆书写更像是一道被反复撕裂又不断缝合的伤口,这种书写一方面是创伤得以进入公共视野的前提;另一方面也注定了它始终处在被再造的动态之中。每一次叙述既是对遗忘的抗拒,也是一次新的诠释与再思考。
数字嬗变:纪念的庄严与轻盈
进入数字时代,对南京大屠杀的纪念与记忆建构也拓展到了数字互联平台。书中对此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一方面,我们不可否认,数字技术和社交媒体的发展进步让庄严沉重的纪念仪式变得更加“轻盈”了。这种“轻盈”首先体现在纪念参与的便利化。比如参与方式的革新:线上公祭活动打破了时空限制,让全球网民得以通过“虚拟捐砖”“数字点烛”等方式参与纪念。在“捐砖行动”中,参与者只需轻点鼠标就能完成祭奠仪式。数字技术的便捷性极大拓展了记忆社群的边界,使纪念活动从地方性仪式转变为全球性实践。
另一方面,这种“轻盈化”却可能带来记忆深度的流失。在短视频平台上,三十万生命的沉重历史被压缩成10秒的“泪目视频”,甚至只是几秒钟闪过的一张全黑图片,用户轻轻划走,随即沉浸在下一个娱乐视频的感官刺激中。记忆的“快餐化”一点点地消解历史的厚重感。而更隐蔽的危机在于算法对记忆的驯化。短视频平台根据用户偏好推送的“历史爆款”,往往强化单一叙事模式:或是血腥影像的重复刺激,或是口号式的爱国表达。当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12秒水滴装置(象征每12秒一个生命逝去)被简化为15秒的“泪目视频”,记忆的厚重感正被流量经济的碎片化逻辑消解。当短视频平台将历史创伤与其他娱乐内容并置时,记忆的庄严性可能被消解为信息流中的普通节点。例如,用户前一秒为遇难者“点烛”,下一秒便滑向搞笑视频——这种认知断裂暴露了数字记忆的脆弱性。
作者在书中的种种分析无一不在提示我们,南京大屠杀的记忆在数字时代的命运最终取决于我们如何平衡“轻盈”的传播力与“庄严”的反思性。当技术既能降低参与门槛,又不稀释历史重量时,数字记忆才能真正成为对抗遗忘的利器。
记忆回响:多元叙事与全球对话
《记忆的纹理》始终将南京大屠杀的记忆视为一块被不断书写、不断打磨的木版,而非静止的石碑。正如书名所昭示的,“纹理”既是时间留下的印记,也是多重力量交织的产物。书中通过剖析记忆与遗忘的辩证关系,勾勒出历史与现代交织下的记忆纹理,其深层目的在于回答一个时代命题:在多种力量相互缠绕的记忆场中,我们应该如何更好地建构南京大屠杀记忆?
对此,两位作者在书中反复强调多元叙事。比如,作者强调多元叙事的必要性:司法的“起源话语”、民族的“纪念话语”、国际伦理的“谴责话语”与对抗日本右翼的“回应话语”,共同构成了一个复调场域。这提醒我们,南京大屠杀的记忆不能局限于某一种叙事模式,否则要么流于政治化,要么沦为符号化。真正的挑战在于,能否在多声部中保持叙事的开放性,而不是让单一的强势叙事重新独占解释权。
此外,此书还站在全球记忆的高度,审视南京大屠杀记忆上升形成“全球记忆”的可能性、阻碍与动力机制。这一洞见打开了我们的视野,明确了南京大屠杀记忆所面临的双重使命:既要守住庄严与厚度,又要面向跨国对话与代际传承。这一视角在现实中也获得了生动印证——2022年,美国明尼苏达州典当行主埃文·凯尔发现并公开捐赠的侵华日军罪证相册,正是跨国记忆对话的典型案例。这位普通美国青年通过社交媒体引发的全球关注,既验证了历史记忆超越国界的传播潜力,也展现了民间力量在突破政治藩篱、重构历史认知中的独特价值。
对话的张力不是缺陷,而是记忆生命力的来源。当凯尔的相册与南京纪念馆的档案形成跨时空对话时,我们看到的正是南京大屠杀记忆超越国家民族,成为全球记忆的雏形。换言之,本书的贡献在于提醒我们:记忆不是通过一次性方案被“解决”的对象,而是需要不断在政治、媒介与伦理的交错中被重塑的过程。从《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的战地报道,到埃文·凯尔的相册捐赠,再到维基百科的编辑争夺,南京大屠杀的记忆始终在动态重构中保持其警示意义。这种既扎根民族历史又面向人类共同体的记忆实践,或许正是我们在全球化时代守护历史真相的最佳路径。
总的来说,《记忆的纹理》一书兼具理论与实践意义,不仅为南京大屠杀研究提供了创新的媒介分析框架,更对当代社会的记忆政治提出了深刻反思。该书通过细致的史料爬梳与前沿的理论对话,展现了历史记忆如何在媒介技术的演进中不断重构,既揭示了权力对记忆的形塑机制,也为平衡记忆的公共性与个体性、全球记忆建构等提供了建设性思路。其价值不仅在于解构既有的记忆叙事,更在于启示我们:唯有保持记忆的开放性与反思性,才能让历史创伤转化为面向未来的精神资源。



600bd524-6a81-498b-8e10-6aff1cc18895.jpe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