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董小玉、何艳
在当代艺术展览中游走的观众,常常会陷入一种认知困境:面对那些既不“悦目”也不“和谐”的作品,是否还能用“美”来评价?英国普利茅斯大学艺术史系教授伊丽莎白·普雷特约翰的《美的,艺术的》,恰好从深远的角度回应了这一话题。这部著作不仅梳理了美的概念史,更构建了一场跨越千年的美学对话,邀请读者重新思考这个看似简单却无比复杂的问题——艺术是否需要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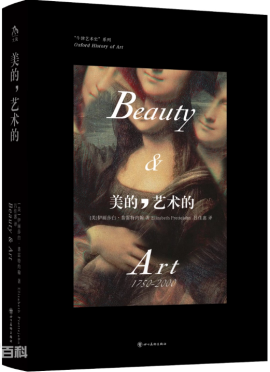
美的谱系学:从客观法则到主体觉醒
伊丽莎白·普雷特约翰带着独特的学术洞察力去解构美的历史。她敏锐地指出,柏拉图的“理式美”与亚里士多德的“有机统一”理论,共同构建了西方美学最初的二元框架——前者将美视为超越性的永恒真理,后者则关注艺术作品的内在结构。这两种充满张力的美学法则在中世纪演变为神圣美与自然美的辩证对立,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在阿尔贝蒂的《论绘画》中获得创造性结合。
除了对最初客观法则的揭示,伊丽莎白·普雷特约翰在对助推个人主体性发展的启蒙美学阐释上,也超越了传统的康德解读。她将康德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与同时代英国经验主义美学家埃德蒙·伯克的“崇高论”并置,揭示出18世纪美学革命的双重轨迹:一方面是对审美判断的哲学纯化,另一方面是对美学体验的心理探索。这种并置使我们看到,浪漫主义画家如弗里德里希的作品《雾海漫游者》中,不仅有个体意识的觉醒,更有对伯克式“愉悦的恐惧”的视觉转化。
至此,伊丽莎白·普雷特约翰施展她渊博的知识体系与清晰的行文思路,让我们得以由远及近地层层探寻“美”之发展的历史谱系,以及了解不同时期美学发展的侧重点与超越性;并且在创作主体与呈现客体的辩证结合中,学会从主客观的不同视角去发掘作品中美的可能性。
现代性的悖论:在解构中重建美学价值
伊丽莎白·普雷特约翰打破了“现代主义等于反美学”的简单叙事。她指出,即使是最激进的达达主义,其反美学姿态仍是对美的另一种关注方式——通过否定来确认。杜尚的《泉》并非简单地否定美,而是将美的判定权从艺术家转移到观众与艺术体制,这实际上拓展了美的可能性领域。
作者对格林伯格形式主义理论的批判尤为犀利。她揭示出现代主义“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背后所隐藏的美学教条:将“创新性”本身神圣化为另一种美的标准。这种洞察解释了为何波洛克的滴画虽然抛弃传统美感,却发展出关于“过程之美”的新范式。现代艺术对美的解构,本质上是一场美学的创造性破坏。
由此可见,伊丽莎白·普雷特约翰的研究揭示了现代性美学演进中深刻的辩证张力,解构与重建并非对立的两极,而是同一枚硬币的双面。现代艺术的革命性不在于其反叛姿态,而在于它通过自我否定实现了美学范畴的拓扑重构,使“美”在废墟中生长出更繁复的根系。
艺术的伦理:当代美学的弥散与重生
在论述当代艺术时,伊丽莎白·普雷特约翰展现出令人钦佩的理论包容性。她将杰夫·昆斯的媚俗美学与埃利亚松的生态艺术并置讨论,揭示出两者共享的美学策略:将传统“非艺术”的感官体验合法化。昆斯通过夸张的俗艳质感解构高雅与低俗的二分,埃利亚松则通过气象装置重建人与自然的美学联系。
书中对全球美学流动的分析尤为精彩。日本“物哀”美学在村上隆作品中的转化、伊斯兰几何学在当代建筑中的复兴,这些案例表明21世纪的美学正在形成一种“翻译中的传统”。美不再是被动继承的标准,而成为不同文化语境间主动对话的产物。这种全球化视角使本书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的美学叙事。
伊丽莎白·普雷特约翰引导我们思考的是一个比美学更根本的伦理问题:当艺术彻底抛弃表面之美的追求,它是否也切断了与人类普遍情感的联系?本书的深刻之处在于,它既不怀旧地呼吁回归传统美学,也不激进地拥抱彻底的反美学,而是指出第三条道路:美作为感知艺术,要与接受者之间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共情空间”,从而使得艺术避免沦为封闭自恋的系统。
在人工智能生成艺术、虚拟现实体验日益普及的今天,《美的,艺术的》不仅梳理了过往的美学史,更启示了未来。当技术可能彻底改变艺术的生产方式时,伊丽莎白·普雷特约翰提醒我们:美的本质或许就在于它永远不能被完全定义,它始终作为艺术的隐秘维度而存在。正是这种辩证思考,使本书成为理解当代艺术困境与美学复杂性的必读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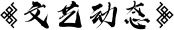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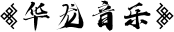
600bd524-6a81-498b-8e10-6aff1cc18895.jpe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