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周勇
作者前记:又到清明。几年前的清明之日,曾作一文,以祭奠父亲、老师和先辈。如今,母亲也已故去,与父亲团聚,长眠于地下。今又清明,回想离开父母的那些日子,很短,也很长。今以旧作,缅怀父亲、母亲,也缅怀老师、先辈。

今天,清明。
上周,妈妈说,去看你爸爸要早点,他是个急性子,不然会念:“他们啷个还不来哟!”因此,4月3日,我们全家就提前去了那个清幽的地方。父亲和他的父母、姐姐长眠于此。没有坟头,没有墓碑,没有鞭炮,没有纸烛,只有两株高大的桂花树陪伴着他们,而那如盖的浓荫则给我们以庇护。
斜阳下,黄色、白色的菊花,精精神神,格外灿烂;陈年的茅台,浓香四溢,引得旁人啧啧称道。口中念念的是先人的名字,缓缓流淌的是心灵的对话。这,就是父亲的心愿。
三年了,父亲仿佛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们。此刻,他似乎一如在世时的恋家、孝亲、厚友、勤业,微笑着、静静地在那里注视着我们。
父亲享寿95岁。2014年12月6日,他要我把已经交给我准备印制的、由他搜集编纂的《沁园春•雪》资料集拿回家来,他还要再改一改。临走时他给我说,我要走了,你要有思想准备。由于他的状态一直稳定,我们谁都没有在意。五天后的12月11日,他果真静静地去和他的父母团聚了……让我们经历了人生中最痛彻的时光。


今早起来,窗外雨大风急。这几天,南方多雨,而北京有雪。南方多雨,古已有之,“清明时节雨纷纷”嘛。而北京有雪,则甚为少见。这倒让我能够清清静静地坐在家里,过一个清清爽爽的清明节。
小时候,邹容是一条马路。
那时我家先后住在临江路、临江支路。每到礼拜天,父亲就要牵着我和姐姐的手,走过民族路,穿过邹容路,来到民权路,进到新华书店、古籍书店,看书、买书。从那时起,我就晓得解放碑有一条马路叫邹容路。
读书时,邹容是一个名字。
我小学住校。毕业后,我上了29中。这所学校就在邹容路的起点上。我第一次在课堂上知道了,“邹容”是一个人的名字,门口这条马路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
再后来,邹容是一段历史。
1979年,我考进了四川大学历史系,从重庆的邹容路走到了成都的望江楼。隗瀛涛先生给我们讲辛亥革命史,我才真正地知道邹容是个了不得的人,创造了一段了不得的历史:中国民主革命理论的形成,特别是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制定和实验,经历了孙中山提出──邹容发展──同盟会政纲确定的轨迹。这是邹容一生最大的贡献。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先生当了大总统,专门作《祭蜀中死难诸烈士文》,称:“惟蜀有材,奇俊瑰落,自邹(容)至彭(家珍),一仆百作,宣力民国,厥功尤多。”他追念“邹容当国民醉生梦死之时,独能著书立说,激发人心”,功勋卓著,命令“照陆军大将军阵亡例赐卹,并崇祀宗烈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主席亲自为邹容编了一本书,1958年成都会议期间,发给参加会议的全体高级干部。他说,“邹容,他写了一本书,叫《革命军》,我临从北京来,还找这本书看了一下。他算是提出了一个民主革命的简单纲领。”他还说,“邹容是青年革命家,他的文章秉笔直书,热情洋溢,而且用的是浅近通俗的文言文,《革命军》就很好读,可惜英年早逝。”
后来我到过日本,去过北美、欧洲,我发现,无论海内外,无论东西方,邹容都是一个真正能够在中国近代史的“正史”中写下独立篇章的人。在重庆,只此一个。
工作后,邹容是我的事业。
在川大读本科时,我就在隗瀛涛先生的指导下研究重庆开埠的历史,在探究开埠的作用时,我专门写了《邹容和他的<革命军>》一节,1982年《重庆开埠史》出版。后来我继续在隗先生指导下研究近代史。当时正值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之后,辛亥革命研究方兴未艾。1981年,我父亲在重庆主持编辑出版了《重庆蜀军政府资料选编》,随即着手编辑《邹容文集》。因此,我就同时有了业师隗瀛涛和父亲周永林这两个老师。1983年父亲编的《邹容文集》出版,那是第一部公开出版的邹容著作。1985年,经中央批准,四川省、重庆市举行了邹容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父亲又编辑出版了《论邹容》。
1983年大学毕业后,我回重庆工作。在《重庆开埠史》的《邹容和他的<革命军>》一节基础上,我准备写一部《重庆辛亥革命史》。尽管我拼尽全力,但并不理想。我求诸隗先生和父亲。他们说,邹容只活了20岁,留下的东西太少。资料的发掘还要靠你们年轻人坚持不懈。隗先生风趣地说:“不要着急,说不定哪一天就像四川广汉‘三星堆’一样,挖出一箱子关于邹容的史料来。”
经过30年的努力,隗先生的趣言果成现实----我们真“挖出一箱子关于邹容的史料”。这30多年中,我始终没有放弃重庆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一方面着力于史料挖掘,一方面陆续写了一些论文。2011年我组织团队申报《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重庆丛书》项目成功,蔡斐博士又加入到团队中来。他的硕士、博士论文都研究苏报案,对邹容与苏报案的历史相当熟悉,勤奋好学,视野开阔,外语又好。在课题组同仁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广泛搜集珍藏在中国、新加坡、法国、美国、日本的邹容著作、书信、诗词、书法、篆刻作品,基本收齐了《革命军》的版本,在家父《邹容文集》的基础上,编成了《邹容集》,篇幅是原书的三倍。随后又编成《邹容与苏报案档案史料汇编》(上下卷),共计100多万字。这样就为邹容研究提供了更好的史料基础、史实基础,我的《重庆辛亥革命史》也得以完成。如今,业师和家父均已故去,现在面对他们,我还是交得了卷的。
今天,邹容是一个英雄,与我们血脉相通。
120年前,岁值戊戌。谭嗣同在北京被捕入狱,高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慷慨就义。在重庆, 13岁的少年邹容热泪纵横,悲愤不已。他将谭的画像置于座前,题诗明志:“赫赫谭君故,湖湘士气衰,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
时光流淌120载,又到戊戌。
两轮戊戌,告诉我们,邹容已经跨越时空、重回当下。
邹容富而思进,追求真理。虽生在富商之家,却没有富家子弟的纨绔习气,而是以天下为己任,追求救国救民之道。他勇立潮头,道义担当。有独立的思想,而且始终站在时代的最前列,由爱国主义、民主主义,进而朝着社会主义升华。他血性刚强,兼收并蓄。这种血性正是今天有些人所欠缺的。但是他又不偏执,而是广交时代英才,把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优秀的文化、优良的传统,与世界上先进的民主革命思想熔于一炉,锻造出那时最为先进的思想武器。《革命军》就是中华民族的中国梦。如果不是英年早逝,以他狂飙突进的思想轨迹和敢作敢为的性格特点,还不知会给后人多少更多更大的指引。
4月2日,我东去上海,参加在邹容埋骨地华泾镇举行的邹容纪念馆开馆仪式、研讨会,祭扫邹容墓;4月4日,又西回重庆,参加在邹容出生地渝中区举行的公祭邹容仪式。分明感受到重庆与上海东西呼应,长江相连的态势。
年年清明,今又戊戌。这东与西,父与师,家与国,就这样流淌在我们的血脉之中,代代相传。
是为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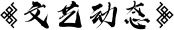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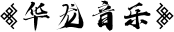
600bd524-6a81-498b-8e10-6aff1cc18895.jpe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