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常克
重庆公安作家程华最近出版的报告文学集《峥嵘》,让我感受到阅读冲击力的看点有好多处,包括作品叙事方式的创新、简练但内蕴丰富的文字个性、流布于文本背后的人性思考等等,每一个点似乎都可以展开来作出分析,获得多选项解读。
如果确定要集中来提炼的话,我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还原。
还原,或者说叫还原现场。还原现场本是一个刑侦术语,但在《峥嵘》此处,则已经衍生出完全不一样的文本表达。
以《回看吴钩霜雪明》为例,作品主写女法医冯白翎一生的办案传奇,跌宕起伏的案侦故事迷雾重重,很多离奇的发案细节堪称闻所未闻。然而作家真正想表达的主旨不仅如此:“其实,我要写的不仅仅是故事,还有以故事为载体的人间百态与人性幽微。”
也就是说故事之外,作家自有开掘,既还原遥远的案发现场,更还原围绕案情而延伸出来的世象种种;而终极的还原,是还原作为作品主角的人民警察那一份朴实本心,那种暗含在日常琐碎与工作风险中的胸襟。进一步讲,作家笔下对每一位普普通通的人民警察的隐喻,是一种于平凡中见出峭拔的英雄胸襟。

一
作家把对生命的观照放在人民警察这个群体上,说他们的工作日常,讲他们的性情和故事,聊他们作为普通人的喜怒哀乐,而看点恰恰就在这里面。
警察的特殊身份注定他们既是普通人中的一员,又是人群中一跃而起的猛士,他们的生命意象由此被赋予平凡而勇锐的解码。《峥嵘》中警察形象很多,有男有女,性格各异,警种不尽相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他们都认为自己不闪光更不英雄,做的工作也是职责所在。作家似乎也并没拿他们当英雄来空泛地颂叹,而是用简洁、朴实甚至带着口语感觉的叙述,还原出他们跌宕起伏的办案历程和真实性情。
还原,说到底就是还原他们在冲锋路上的那一份本我,那种灵魂的温度。
这样我们才能够理解还原的重量,理解作家敞开文字世界,捕捉到故事深处的那些本底信息。作为一部讲述警察人生的报告文学作品,作家的发力在于抽丝剥茧揭开一波三折的神秘真相之后,带出了关于普通人与英雄的一个新的解读窗口。
我注意到作家的一段感慨:“数字是枯燥的,案件名称代号是抽象的,奖牌奖章光芒炫目,但似乎少了某种温度。那些隐于追光背后的细节,那些血与火的淬炼、汗与泪的泼洒,才最值得去端详,去钦敬。我们会因此真正懂得那句耳熟能详的话: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
我的理解是,作家希望抵达这样一种语言宽度——守护生命与平安,从来没有一个白天和黑夜是宁静的;就在我们身边,在我们知道或者不知道的地方,很多故事正在发生或者已经发生,匆匆忙忙的人流中,普通的人民警察和英雄的人民警察每天都和我们在一起。只不过,我们没有觉察到英雄的存在,甚至连英雄自己也不知道他们身上闪耀的光芒。
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峥嵘》给了更多人沉思的开阔地,尤其是关于英雄内涵的沉思:英雄究竟是怎样一种人?他们的日常生活与工作到底是一种怎样的节奏?他们在奋不顾身的紧要关头,是不是也有平常人家的那种牵挂?
凡此种种,我们都希望看见或者听见还原的声音。
还原,是我对《峥嵘》创作需求的阅读理解,我当然相信这也是《峥嵘》从始到终的追寻,即,从还原现场到还原内心。
来看《中成,你是我们的兄弟》,作家在采访札记中说自己最初的心态是“完成任务”,但采访第一天,她就重新作出决定:“我要写好他,要尽力还原他。”显然,冯中成作为一个普通人首先打动了作家,所以她要求自己必须写出最真实最生动也是最普通的人民警察冯中成:“有的人,看似硬朗,固执,有时有些‘不近人情’,当然更不懂圆滑,但他们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对于应当善待的人,他们会无条件不计代价地对对方好。冯中成就是这样的人,外冷内热,严肃的外表下有一颗温热的心。”
应当说作家讲的还原,就是要还原出英雄冯中成作为一位人民警察本色的那些东西,包括性格、价值观、对生命意义的理解等等,也正如石柱县公安局政委姚建龙在接受作家采访时说的那句话:“英雄也是人,是人就有这样那样的小缺点。没有缺点的英雄是不真实的!”
《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写的是获得“全国公安百佳刑警”称号的重庆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打拐支队支队长樊劲松。一位女孩被拐七年,得救后她好奇地问樊劲松:“你怎么找到我的啊?”
樊劲松憨厚地答:“一直找啊,一直找,就找到了……”
一个人,朴实得犹如清泉流动;一位人民警察,他的自述平静得波澜不惊。在这样的还原面前,那些曾经艰难曲折地寻找乃至惊心动魄的碰撞,也才更其令人由衷感佩。
仍然以樊劲松为例,采访札记中写道:“在我的采访经历中,男警流泪的场景很稀有。多数人在讲述办案经过时,会将自己置于执法者、冷静的观察者的位置,而樊劲松给我感觉是:他常在‘警察’与‘父亲’角色之间切换。因为他说过:‘将心比心,如果我儿子丢了,我哪里睡得着,我半夜也要爬起来找孩子啊!’”
这同样是还原,是对一位人民警察内心轨迹的还原。这其实就是通过还原一步步在往深处思考和提炼,最终还原作品的主题指向。然后,作家借由采访札记来完成作品的点题:“‘如果我是那个父亲’‘如果我是那个孩子’……我相信,这才是樊劲松多年艰辛付出的内驱力——设身处地的同理意识,以心换心的职业自觉,为修补一个个残破家庭锲而不舍的高度奉献精神。”
《峥嵘》所表现的多位人民警察的故事本质上还原了一种生命高度,他们日复一日的工作形态也许貌不惊人,但充满人生命运的挑战。实际上,这种文本表意和爱因斯坦说过的一句话意思是一样的:“人只有献身于社会,才能找出那短暂而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
程华本身就是警官,这个身份对她创作公安题材的作品当然会有帮助,但这并不代表她有大把时间来进行安静的文学创作。随便举个例子,比如写《深渊》,作家就用了纯粹电话采访的方式。她一直排斥“非面见采访”,但这次破例了。这是多种因缘巧合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开州距主城300多公里,她只是业余创作,不能为赴开州采访耽误本职工作,但这个案例又着实吸引了她。
据我所知,作家这次电话采访全部利用周末,连续三个周末通电话,每次起码三小时以上采访当年的办案警察,对很多细节都完全摸清楚了。第四周作家写出初稿,开州区公安局当年的办案警察读到后很激动,也觉得很神奇,通过电话采访就把文章写出来了?其实他们不知,这个创作过程对于作家来说是相当熬炼的。
程华告诉我说,我要还原现场,就需要他们提供当时的现场照片,包括当年专案组人员的照片,因为我们彼此没见过也不认识,只好通过这种方式来加深印象,获得现场的感觉。程华说,我甚至要判断他们的性格,判断十几年前他们在悬崖峭壁上的每个动作,说话的语气,我都要了解清楚,全部还原。
一部文学作品有没有揭示出作家希望打开的精神世界,主要看它力图通过人物与事件的矛盾冲突从而提取到的哲学价值和美学意义,这大体上就是我们常讲的作品深度。对叙述对象心灵的揭示,对林林总总生命现象的破解,哪怕只撞击到一个细微,只凸显出一个支点,总之能够带给人耳目一新的文本表意,这无疑就获得了作品的文本价值。
二
但凡公安题材的文学作品,包括小说和报告文学,吸引我们的看点主要来自作家所呈现的精彩故事。具体到《峥嵘》而言,作家不仅要讲好故事,更要还原出故事的现场感和明确的文本探索意识,这等于自我加压推高了创作难度。
从还原的角度来讨论《峥嵘》的文本表达特色,我们会发现,在传统的叙事讲究之外,作家为每一个迷雾般的的故事赋予灵魂之光,从而让读者看得见笔下的哲思,触摸到人性的繁复与幽微,通过层层剥解案情把人性的真相还原出来。很显然,为了达到这个创作目的,作家尝试了多方面的探索,其中一个显而易见的推手是文本建构,就是在主体叙事之前和之后,用了核心导读和采访札来作引导和补充,我称之为回环式文本建构。作家为还原现场,作了从内容到形式的多重布局。
这种回环式文本建构的基本特征,有点类似于工笔画作品中的层层撕染,通过每一种文体的不同特征和功能运用,增强故事背景的烘托与说明,强化读者对故事的理解,由此来多维度支持作品主题的确立。而归根结底,运用这种创作模式的目的,仍然是为了更准确地还原现场,还原叙述对象的内心活动与人格魅力,还原普通人心灵的高致以及他们作为英雄闪现的时候那种生活的原汁原味。
文本建构表面上看是作品在形式上的变化,而实际上可窥见作家的艺术主张及其表达效果。这种回环式文本建构不是为了花式表现,而是作家用心用情近乎“无所不用其极”的一种创作态度。《峥嵘》通过运用回环式文本建构达成了其文本形制和叙述管道的别致呈现,这种探索与创新同时也为同类作品的创作路径提供了参考标向。
来看《勇者的沉默,胜过雷霆万钧》第一节下面这段文字:
“梁新宇倒吸一口冷气,心像被利刃狠剜,生割,碎裂。”
“田里两具遗体,一名是民警,一名是辅警。两人的衣服碎成了布条,露出的肌肉被剧烈的爆炸冲击波撕扯得残缺不全,民警的脸被飞迸的爆炸物打穿,看上去有些扭曲变形。凝固的血、破碎的肉体、散落的瓦片……”
因为有引言部分的导读,我们此时的阅读感觉是精神高度紧张,在忐忑中希望获知案情的来龙去脉和最后破案的真相。硝烟既现,前途未卜,这种扣人心弦的形制设置一上来就令人呼吸急促。
然后是第三节这句:“整整18年,梁新宇先后参与处置过百余起涉爆现场,多次成功拆除各种复杂的爆炸装置,20余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我们无法想象一个人“20余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是怎样一种死里逃生的生命体验,但我们至少懂得,梁新宇的每一天和我们的每一天完全就是云泥之别,他所时时面对的生命考验几乎就是在以命相搏。
作家在后面采访札记中对此发出了一句意味深长的喟叹:“其实,这个20余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排爆手很清楚自己的工作意味着什么,要经历些什么。”
这就是文本建构带给我们的阅读震撼,它不仅还原现场,更还原了一位普通人民警察的英雄虎胆,而这样的英雄每天都出现在我们生活的某个画面之内。
在读《光芒》的时候,尽管斗智斗勇的故事让我沉醉其中,但是真正拨动我沉思的关键词在故事之外,在采访札记。下面这段文字,每一句都点题,都是作家灵魂的发声:“警察首先是人,是人就有人性,就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只是他们的职业素养和反应让其有别于一般群众而已。如能撇开‘英雄’表象而紧抓人性,以己之心度其正常反应,写出来才能让人信服……眼耳手心情感火力全开,全身每个毛孔都像雷达一样打开,逡巡,接收,感知。我以为这是写出真实鲜活的报告文学的必备状态,公安题材如此,所有题材概莫能外。”
这一段文字反映的不是风格问题,而是作品对警察、普通人以及英雄的独到诠解。通观《峥嵘》全书,应该说每一个故事都自有引人入胜处,书写方式也在不断求变,但核心贯通点,仍然是作家紧贴情节推进而努力还原人民警察的真实属性——他们也有干累了吃不消了的疲惫,也有长途跋涉却一无所获的沮丧,也有远离故乡家人的无奈与惦记,也有得意忘形的欢叫,也有义愤填膺的爆粗口,总之他们工作与生活的很多节点,都从文本里面还原出来,还原为活生生的每一个人。
也就是说,作家一方面在努力还原现场,另一方面更是在不遗余力地还原人民警察朴实的心灵影像。我想,这是作家的初衷,是作家希望到达的表意高度。
现在,从这种回环式文本建构的精心设置上,我同样清晰地找到了答案。
三
一个人对平凡与神奇、普通人与英雄之间的价值读取,在《峥嵘》这里是用故事来还原的,文本既可以是独立的一篇,也可以是对人物群像的整体回眸,也就是用很多篇同一题材的作品来形成叙事的阵列,这是一种宏大,我们除了得到与作家同样的精神共鸣,更重要的是还原了对英雄本色的思索。我们的心灵回响,发端于自作家笔下简洁、新鲜并且收放自如的文字调遣。
对作家而言最终都要靠文字来说话,作家的思想深度和创新无一例外总要凭借文字表意来延展,这是文字的法则。我自然地联想到一个人,著名作家韩小蕙,她在谈创作体验时说过:“我始终坚持认为,文字不是一切别的,而只是呕心沥血的产物——更严格地说,文字是一个人生命的外化形式,每一个字都是用一滴血换来的。”
我不知道这段话是否可以对应作家程华的文字历程,但我确实在分析《峥嵘》的形式与内容时,非常明确地感觉到那里面有叙事技巧,但又超越了技巧。这当中包括句式的简洁、特定的场景显现、办案警察触景生情的对话和情绪波动等等,都集聚着作家的诸多文字诉求。
来看《深渊》中一段:“案子是要办的,命也是要紧的。民警在山下四处寻找,总算在一家小店买到了防滑链。顶着漫天飞雪,‘老爷车’蜗行几小时后爬上了山顶。”
注意这一句“案子是要办的,命也是要紧的”,初看它是作家的话语方式,但实际上它在反映办案民警千辛万苦的同时,深意在于暗含人民警察的智勇与达观,往深了说,就是一种精神气度。
通过文字效果来演绎作家的深层次观察,这在《峥嵘》的叙事中随处可见。我们理解为文字的技术运用也可以,理解为作家的文字风格也行,但我渐渐发现,透视这文字的底色,我们看见的是作家的温情。
就文学作品而言,在文字里面直接代入作家情绪这相对是容易的,但能够让文字自然而然流露出情怀,投送出作家发乎于心的温情,这显然就是另外一回事,所谓文字的厚度,大抵就包含了这一类介质。
这样的温情倾向,在《深渊》的叙述中尤其突出。作品开头就推出两个场景,几句话就入巷,然后顺势引入主体叙述。我们会发现,作家笔底有体温,她对受害者的怜惜与同情,往往不正面来表达,而是通过文字对应的意象,几个字或者一段话便表露到位。如这一段:“寻找小猪尸体那天,阳光很亮,但感觉不到一点温度。十几个民警押着周全上山找到了那个天坑。站上面用电筒一照,黑乎乎的坑里依稀可见一只口袋……”这一段是令人窒息的,更是令人义愤的,它还原的是冷酷的现场,它带给我们超越愤怒的那种情感与深思。
文本的巧构和温情的流露,这两个表意元素帮助作家来到了属于她的那一片文字时空。文字特色跟表意推进能够表现得干净而含趣,这其实是有难度的。能够把性情的某一面有意无意整合于文本当中——尤其是比较严肃的公安题材作品——这与其说是一种功夫,倒毋宁说,这是温情的闪烁。
富含温情的文字在《峥嵘》中随处可见,是因为文字背后藏着文字,故事之外另有故事。温情融化在文本中就形成了作家的独有文字风貌,很多句式甚至带着作家独一无二的幽默感。
我在读《光芒》的时候,被作家的智巧弄得忍不住想笑:“很多数人并不知搞技术的李江具体在忙些啥,也不清楚他整日两眼发直近乎失语的状态到底意味着什么。直到十几天后一个中午,正想上楼去实验室了解进展的技术大队大队长陈恩一头撞见手舞足蹈从实验室飞奔而出的李江。这个三十大几内向羞涩的眼镜男一把拽住陈恩猛力摇晃:‘搞着了搞着了!’(方言,即成功了)”
“两人霎时眼冒星星:‘啊,搞着了搞着了!’”
“全支队瞬间也欢腾了:‘搞着了搞着了!’”
《隔空捉鱼》中讲到抓住了冒充“美女”网骗的嫌疑人时:“雷洋貌似平静地看着他,心头翻江倒海。撞你个鬼,明明就是抠脚大汉嘛。虽然早有思想准备,但亲见天天在网上和自己卿卿我我的‘美女’就这副德行,雷洋还是忍不住一种吞了苍蝇的恶心感……”
作家似乎是在寻找一条路,带着自己的灵魂追问与明显的情绪代入,然后释放出独立的文本画质。我感觉到作者的文字符号正在日趋定形,识别度越来越具有自主性,这当中最有特色的蕴藉,就是通过明确的文字性格来表现作家心灵的亲近。
亲近谁?当然是英雄。那些看上去并不像英雄的英雄。
通观《峥嵘》,这与其说是一部长长的文字,倒毋宁说这是一首写给英雄的颂歌。作家奔流在笔下的真情实感,一览无余。
因而,我确实感觉到一种阅读的惊喜。
有一次和作家程华摆龙门阵,她说,自己想要的是痛快的、简洁的、呼呼带风的那种文字手感。
看来多年以后,作家确实找到了自己初步认同的话语方式,那是一种温情与力量捏合在一起的文字质地,从根本上讲,那也是一种对作家精神领地的还原。
而作家的改变不是说来就来的,需要大量创作实务做铺垫,甚至需要历经翻山越岭的痛苦领悟,当然特别需要的更是一种境界疆域的还原——首先还原自己骨子里面的温情,紧接着才是文本展现——这个时候,文字的温情与力量才是浑然一体的。这就是说,给人印象深刻的文字都不是写出来的,而是熬出来刨出来磨出来的。这当中,常常饱蘸着作家甘苦自知的苦功。
叙写平凡人中的英雄,很多时候,作家的状态也需要犹如冲锋陷阵。这让我想起2018年春,我和包括程华在内的五位作家联袂撰写报告文学作品《热血忠诚——“时代楷模”杨雪峰故事集》,从采访到出稿一个月,那阵仗堪比急行军。程华后来在 《一次震撼心灵的创作经历》一文中回忆说:“当时采访书写之艰辛,在我20多年创作生涯中亦属少见。最艰难疲惫的日子里,我从清晨七点写到凌晨两三点,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我把10岁的儿子撂在一边,家务事全部交给丈夫和家人。为维持大脑长时间清醒,一杯浓茶喝成白开,紧接着又泡上一杯。一段时间我头痛欲裂无法安寝。”
程华坦言,那次参与集体创作的另外一层标杆意义在于,完全激发了她的报告文学创作渴望,直接引出了后来多篇目报告文学作品发表。
在整体感觉上,作家程华近年来的报告文学作品确实大有变化,从文字到表意都焕发出新的生长,《峥嵘》可谓一次快意集纳,作品刻画出平凡人灵魂的容纳与广阔,反映出作家的疼痛与告慰。读这样的作品,能够读出生动中的深邃,幽默中的深情,智巧中的深度,这是作家对生命哲思的一次浓郁的沉浸。
更进一步说,这一方面是文字所透露给我们的那种高远,另一方面也表达了作家对生命现象最朴实的观照,而这正是文本高度。
现在来说不足。我目前感觉是作品的文字延伸感仍嫌不够,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作家在主体叙事部分的内心思考还可以加强,该说的话要说够,该提升的人物高度要明确地提升起来,从而在更开阔和更深刻方面表现出更流畅和自如的话语感;第二,在追求文字简洁的同时把握好文本气息的丰润度,体现在节奏中就是文字的张弛与收放的艺术处理,可缓则缓,当疾则疾,从而显现出文本风格的统一性和沉厚质地。
总体而言,作为一位女性作家,程华通过《峥嵘》带给读者一个深邃而离奇的人世镜像,她把关于生命的哲学思考生动地交还给每一个故事,让情节和人物来说话,这既考文字功力,更见出洋溢在文字其中的情怀。用作家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不喜欢用大词,那种空泛的不特定的语言,宁愿用比较细节的词语来表现,追求文字背后的这种感情。
这实际上跟意大利作家埃莱娜·费兰特的观念同位。
“带着清醒的思考,坚定的目光,带着勇气去写”,对于作家程华来说,这恐怕是必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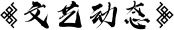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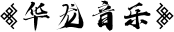
600bd524-6a81-498b-8e10-6aff1cc18895.jpe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