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董小玉、骆逸欣
“平台已成为我们时代最强大的经济和社会力量之一,它们重塑了工作、消费、社交乃至民主的形态。”这是加拿大学者尼克・斯尔尼塞克在《平台资本主义》中对当代社会的精准论断,它们不仅重构了工作与消费形态,也改写了社交与民主的运行规则。本书深入剖析了平台作为一种新型经济组织形式,是如何通过数据、算法与资本的结合,重构全球经济格局与社会关系。它不仅揭示了平台资本主义的运行逻辑与内在矛盾,更对其引发的劳动异化、数据剥削、垄断加剧等问题展开深刻批判,为我们理解数字时代的生存困境与破局方向提供了关键指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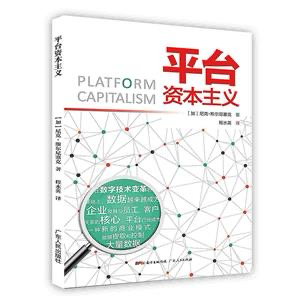
时代之基:平台资本主义何以兴起?
尼克・斯尔尼塞克在第一章便点明,平台资本主义的崛起是资本主义应对三次重大危机的历史结果,每一次危机都推动着资本与技术的深度绑定。正如齐泽克所言:“资本的局限就是资本自身”,这种内在矛盾恰恰驱使着资本主义通过商业模式革新,实现“浴火重生”,而平台便是这场重生的核心载体。
平台的兴起,深植于20世纪70年代信息技术革命。彼时,资本主义国家深陷滞胀危机,美国将信息网络技术视为“提升竞争力的替代手段”。在政府扶持下,资本涌入电子行业,为日后互联网的商业化埋下伏笔——这本质上,是资本在增殖焦虑中的一次战略转移。九十年代,为应对产能过剩,美国推行“资产价格凯恩斯主义”,推动互联网从非盈利性应用走向商业化浪潮,亚马逊、谷歌等平台雏形显现,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成为平台资本主义全面爆发的催化剂。数字平台凭借其数据变现的高效性,成为大量剩余资本涌入的新领域。同时,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逐步成熟,大幅提升了数据收集与分析的效率,平台得以突破传统产业的时空限制,渗透至生产、流通、消费的每一个环节。这一时期,平台的快速扩张,核心驱动力仍是资本的增殖需求,辅以技术进步与“网络效应”的助推。
逻辑之核:平台资本主义何以运转?
平台资本主义的运转,在于构建“资本-数据-算法”三位一体的闭环运行体系,通过数字技术将各个领域转化为可被量化、提取与变现的资源。尼克・斯尔尼塞克强调,平台并非单纯的“中介”,而是通过搭建数字基础设施,成为连接用户、生产者、服务者的“数字守门人”,并在此过程中完成对数据的垄断性占有。
从运行逻辑来看,平台的运作可分为三个关键环节:
首先是“数据捕获”。平台以免费服务为诱饵,吸引用户主动或被动地贡献个人信息。那些看似零散的“数字足迹”,在算法的编织下汇聚为具有高价值的“数据资产”。
其次是“数据处理”。通过机器学习与大数据分析,算法将数据转化为精准的用户画像。平台一方面通过“个性化推荐”增强用户粘性;另一方面优化“资源分配”以提高平台效率,如网约车平台通过算法调度司机与乘客,外卖平台依靠算法规划配送路线。
最后是“资本变现”。平台将数据与算法创造的价值,通过广告投放、佣金抽取、数据交易等方式转化为资本收益,并以此巩固自身的垄断地位。平台不仅充当着数字守门人的角色,更是价值的分配者:既对用户数据进行二次增值利用,也从服务商中抽取高额佣金,形成“吸引用户-获取数据-优化算法-提升收益-扩大规模”的闭环。
正如尼克・斯尔尼塞克所言,平台资本主义的崛起,本质是资本借助数字技术,将剥削范围从传统工业领域拓展到了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困境之思:平台霸权何以引发危机?
平台资本主义在带来效率提升与生活便利化的同时,也悄然编织出一张“数字牢笼”,引发一系列社会危机。其影响早已超越经济范畴,渗透至劳动、隐私、公平乃至民主等社会根基。
从平台来看,资本逐利的本性使其陷入“自我反噬”的困境:全球广告拦截软件的蓬勃发展促使如谷歌、Facebook等依赖广告收入的平台面临不稳定挑战,迫使其可能转向直接支付模式,加速生态封闭,最终丧失核心竞争力;而Uber、Deliveroo等精益平台,依赖“低价服务+灵活用工”快速扩张,却把运营成本与风险转嫁给劳动者,直接冲击其核心盈利逻辑。
于用户而言,其权益也在这一体系中遭受多重侵蚀:平台将传统的雇佣关系转化为“灵活的零工关系”,看似赋予劳动者自由选择的权利,实则将劳动风险完全转移给个体。在隐私与数据领域,平台的“数据捕获”已突破合理边界,演变为无孔不入的“数字监控”。这些数据不仅被用于商业变现,还可能被用于政治操控与社会规训。
在市场层面,平台凭借“网络效应”与“数据垄断”,逐渐形成“赢者通吃”的垄断格局。大型平台通过收购竞争对手、交叉补贴等手段排挤中小平台。这种垄断不仅抑制市场竞争,更赋予平台“规则制定权”。它们可随意调整佣金比例、修改算法规则,而用户与小生产者却无力反抗。当少数平台掌控数字命脉,社会资源的分配便愈发向资本倾斜,贫富差距也随之进一步扩大。平台与用户的双向困局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平台资本主义的核心危机。
破局之路:如何走出平台资本主义困局?
面对平台资本主义的霸权,尼克·斯尔尼塞克并未直接给出答案,而是用审慎的笔触勾勒出多条可能的路径,却又揭示其内在的局限。这种“提出即否定”的辩证思考,恰恰是《平台资本主义》最具深度的部分,也使关于“破局”的探讨超越了“找答案”,转而直面治理的复杂性。
有人主张以“合作平台”对抗垄断趋势,但资本逐利的本质注定了此类尝试难以持久,大型平台常借合作之名,行渗透之实,如谷歌曾以“数据共享”为由,变相掌控中小广告平台的流量分配,使合作沦为“以合谋代竞争”。
对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国家干预”,作者虽然承认“守门人”的作用,却也点出关键矛盾:一方面,部分国家受平台资本游说影响,监管政策易向资本倾斜,难以真正约束巨头;另一方面,过度监管可能抑制技术创新,甚至导致政府借“监管”之名垄断数据,形成新的权力中心。
最后,作者将希望寄托于“创建公共平台”的构想——由大众拥有与监管的平台,摆脱监控与资本的逻辑。这意味着国家将资源投入其中作为公共事业发展,将平台收集到的数据实现资源分配、与民主参与,推动技术向更具包容性的方向发展。
《平台资本主义》最核心的启示,或许是帮助我们打破对平台的“工具迷思”——正确认识平台,是避免其走向垄断的第一步。平台从来不是中立的“技术载体”,而是资本逻辑与技术权力交织的产物。看清这一点,我们才能超越“便利即合理”的肤浅认知,正视平台垄断对劳动尊严、隐私自主与社会公平的侵蚀。本书让我们明白:平台的价值,本应是服务人与社会,而非成为资本垄断的工具。唯有先正确认识平台的本质,再以个体行动汇聚成集体力量,才能守住数字时代的公平底线,让平台经济真正走向开放、共赢的未来。
 分享成功
分享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