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董小玉、涂涵钰
《初识传播学:在信息社会里正确认知自我、他人及世界》是一本经典教材,由传播学者埃姆·格里芬根据他在美国惠顿学院数十年的教学经验撰写而成,先后经历多次再版。它的第七版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展江译介成中文。在《初识传播学》中,格里芬教授不仅对32种传播理论进行了脉络清晰、深入浅出的讲解,还链接了新闻传播学理论的学术前沿,为新闻传播学学子提供专业教育的同时,也致力于加深普通人对传播学的认识和重视,将传播理论转化为日常生活中的工具,更好地理解在信息社会中人与社会的关系、处理在网络空间中可能遭遇的困境,在信息时代更好地应对各种挑战。为深入体会该书内涵,西南大学师生就此展开对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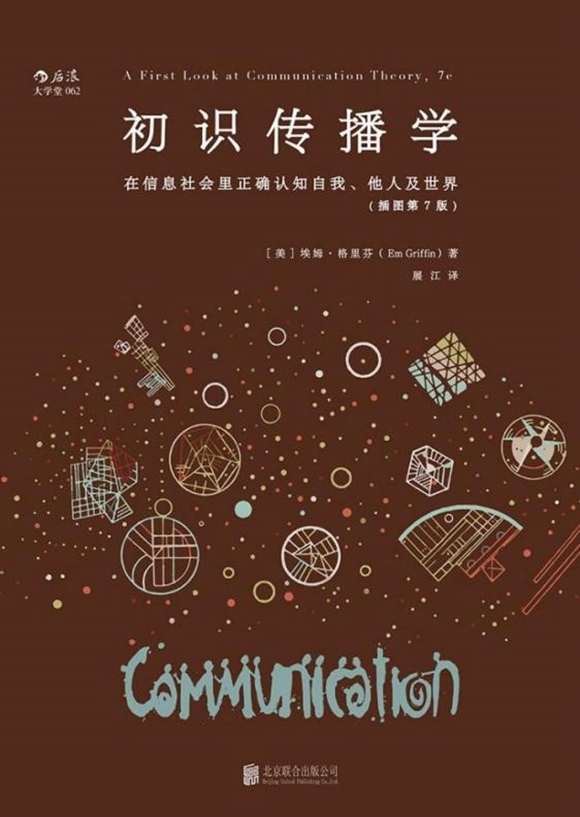
研究生涂涵钰:在《初识传播学》一书中,作者从传播学七大学派出发,先后向读者介绍了32种传播学理论,包含了人际传播、影响力、群体和公共传播、大众传播和文化语境五个方面的内容。结合当下的媒介环境,请问这本书最触动您的地方在哪里呢?
博士生导师董小玉:《初识传播学》所介绍的传播学理论很全面,涵盖了传播学各个流派的重要思想,时间跨度也非常大:从世界大战时期、传播学刚刚兴起时有关人际互动和影响力的相关理论,到千禧时代,人类面对计算机和互联网出现而开始的对技术反思等,这些理论对当今社会有着深远的意义。如今,媒介技术的变迁是有目共睹,它在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今年2月15日,Open AI发布的人工智能文生视频大模型Sora推出后,再一次引发了人们对于人工智能的智能化水平的热议。从ChatGPT对人类语言的逼真模仿,到Sora对线下场景的敏锐捕捉与创造,都让我们深刻感受到未来人类与技术之间的紧密关联,这将重构我们对现实生活的认知图景。正如计算机科学家尼古拉·尼葛洛庞蒂所说:“计算不再只是计算机和技术,它决定我们的生存。”在这样的语境下,《初识传播学》中对于传媒生态学的理论介绍值得我们深思。
长期以来,以美国实证研究为代表的“经验主义范式”和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批判主义范式”是传播学领域的两大主流研究范式。千禧年以来,技术主义范式逐渐崭露头角。传媒生态学,现在学界多称为媒介环境学,正是在这一范式的影响下应运而生,提出了一系列的传播学理论,而媒介环境学主要探讨技术和技艺、信息模式和传播编码在人类事务中扮演着主导角色。在麦克卢汉、波兹曼和梅洛维茨为代表的三代学者的不懈努力下,该学派的理论体系日臻完善。1968年,波兹曼在媒介环境学会成立时指出“媒介环境学研究人的交往、人交往的讯息及讯息系统。具体地说,媒介环境学研究传播媒介如何影响人的感知、感情、认识和价值。它试图说明我们对媒介的预设,试图发现各种媒介迫使我们扮演的角色,并解释媒介如何给我们所见所为的东西提供结构。”
在《初识传播学》中,作者着重介绍了麦克卢汉的相关思想,例如“媒介即信息”这一关键论断。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会关注媒介传递的内容,而忽略了媒介本身,对此,麦克卢汉指出:“媒介内容就像是窃贼手中鲜美多汁的牛肉,其用途是分散思想领域看门狗的注意力。”与该观点的逻辑起点相似,传媒生态学正是将长期以来被人们所忽略的技术与媒介作为研究的重点,把媒介作为环境展开研究。在当下,媒介与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其从不可见的黑暗中彰显出来,媒介环境学成为传播学研究的热门,同时也呼唤着大众在日常的媒介实践中,重新认识媒介和技术所发挥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并警惕技术给人类带来的威胁,正如波兹曼所说:“每一种技术既是包袱也是恩赐,不是非此即彼的后果,而是利弊同在的产物”。
研究生涂涵钰:《初识传播学》的书皮上有这样一句话——“在信息与人类须臾不可分离的今天,传播学是人人都必须掌握的一门艺术。”您怎么看待这种观点?
博士生导师董小玉: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手机成为我们与家人朋友保持联系的纽带,短视频让我们足不出户就能洞悉世界各地的新闻动态。在这个互动的世界里,我们可以获得陌生人的点赞,也可以对他人的行为进行点评,我们是观看者,也是参与者。直播、爆料、数字经济、虚拟现实等等新鲜体验已变成我们生活的常态,然而,这些改变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不可回避的矛盾和失落,正如海德格尔所说:“人们在技术座驾的逼促下按照技术的逻辑来遮蔽世界。”
而这一切,都与传播学息息相关。对于智能化时代中的每一个人而言,学习传播学是在一个全新的“信息国度”中,学会一门能够帮助你畅游其中的重要工具。当我们了解到传播的规律和发展逻辑之后,其生活将会变得更加自如,以享受技术带来的便利。正如乔姆斯基所说:“新媒介成为人类解放的工具还是支配人类的工具,关键看媒介掌握在什么人手中。”
不仅如此,学习传播学还能够教会我们如何在智能化社会中保持理性。面对网络暴力、群体极化、隐私泄露等媒介困境,学者们常常会提到公众媒介素养提升的重要性,以《初识传播学》为代表的传播学科普书籍则能够帮助民众提升自己的媒介素养。艾吕尔认为,不应该用技术标准取代道德标准,而应该用道德标准来应对技术。在技术不断发展、技术伦理问题不断涌现的当下,公众对传播学的认知同样也将帮助他们在新的技术环境中保卫人的主体性、捍卫人思考和参与的权利。


